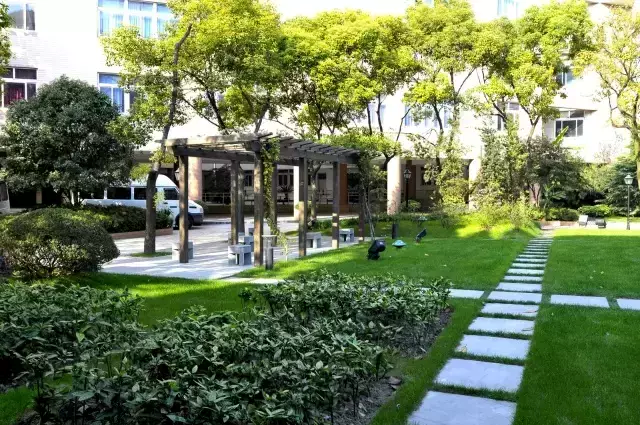2016年,复旦附中海外基金会的第十年。
为此,《复旦附中人物》将在今年以我的附中记忆为话题,分享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校友或老师们眼中的附中故事。
今天我们要分享第一篇“附中记忆”——《附中是什么》作者丁元元,2002届复旦附中校友,现为媒体记者。
活到30岁出头,人生好像也没有多大的亮点,至今还会被说起的一件或许是高中三年就读了上海“四大名校”之一的复旦附中。也是因为我的“乏善可陈”,长辈说起我至今会把这段成年往事当做得瑟的谈资。有人说这所学校都是尖子生,有人说在里面一定压力很大,再知道一些“内情”的,觉得我是进了高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,日渐堕落。这些说法看似都对,却也不十分完整。但回想起1999年—2002年在复旦附中的三年经历,确实是人生中十分重要和难忘的阶段,而这一切记忆的美好,都不在于什么成绩啦,学习啦,而在于在自己15—18岁的阶段,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更了解了自由的可贵。
男生女生
高中是情窦初开的年纪,但“早恋”二字似乎又是这个时代最敏感的话题。不过,在附中,这似乎从来不是困扰。那时候虽然我们班主任比较保守,课桌安排的基本都是男男、女女同桌,但男生女生之间只要不是太内向,真的没有太大的隔膜,一起玩通宵也再正常不过。很多人就整天想着自己喜欢哪个异性同学,全班都知道,老师也知道,好像也没什么。
公开、半公开的情侣很多,一位和我关系很好的老师说起哪两位男女同学恋爱,竟然说:“这种事情嘛,作为老师,我不管也不好,管太多也不好。“有一次集体活动去浙江,不知谁怂恿的,男生给自己暗恋的女生敬酒,很多女生完全是“躺枪”。虽然所有的“故事”都在班主任面前暴露了,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后果。最牛掰的是高三时候一对小情侣,每天广播操散场时,总有牵着手在全校同学面前走过,面对这样的“秀恩爱”,即便校长站在台上,似乎也无可奈何。
有一段生物课,同学要在课前轮流做一个小的“报告”,某君的主题比较奔放,记得有一段说到人是唯一面对面进行性行为的动物,引发全场哄堂大笑。生物老师也没觉得有啥,后来竟然有人打了小报告。班主任找此君谈心,他十分坦然地说:“我只是讲了一些性方面的学术问题。”班主任反倒无语了。
我们寝室有一个男生,曾在熄灯后大声询问对面一个寝室的男生:“打过手枪还算是处男吗?”声音传遍了楼道,从此被调笑很多年。体育课我们的体育老师叫郑芒,现在已经退休了。高一第一堂课,他就提出要求,以后每一堂课,男生都必须穿短裤,包括冬天。他甚至解释说,有的家长为了“对抗”他的要求,就买一套三枪牌棉毛裤,把裤腿剪了,弄成三枪牌棉毛短裤——但是,只要是短裤就行。
后来每到冬天,只要听到男厕所传来阵阵惨叫,我们就知道,又是哪个“郑芒班”要上体育课了。现在想来,也许这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?
冬天要脱,夏天当然更可以脱。有一次夏天跑1000米,郑芒说:“赤膊跑,成绩可以减5秒(提高5秒)。”那时候我们自觉身材都还好,于是就脱了。据说那一段,教学楼里很多班级都不好好上课,没事看操场上有没有裸男跑1000米。
附中背后有一条小路叫国权后路,传说当年蒋介石撤离上海走的就是这条小路。有一次,我们在课上,郑芒让我们喊个口号,指着国权后路上一个路过的中年大妈说:“这个人回头了,就说明足够响亮,可以自由活动。”我们用足吃奶的力气,大喊一声,估计把路上大妈吓得不轻,然后就解散踢球了。
课外阅读
附中的老师,很多都极有个性。最有名的老师之一是语文组的黄玉峰,韩寒的成名路上,他也有过不少助力。我去听过几次他组织的报告,还听他说过自己在狱中找书读的故事。不过三个年级三个语文组,其实各有一位旗鼓相当的领军人物,彼此之间“钉头碰铁头”。
但是很多看似平和的老师,其实也非常有智慧。我曾被隔壁班的陈俊社君(此人现在法国安盛,其实是“安肾”,一度自称“三肾道人”)拖去陈维扬老太太的“掌故趣读”课上。印象最深的是,老太太给我们看的何清涟的文章,那时候就开始接触《人口:中国的悬剑》、《中国现代化的陷阱》、《我们仍在仰望星空等》等。那时候鹿鸣书店还不在国权路上,更不是在南区,记得就在政修路上的一个小门面,有人专门去问:“有没有何清涟的书?”书店的人说,何清涟的书都被禁了。
那时候陈俊社君他们手里有本小册子,读到有思想性的内容就会在上面写点感受,互相交流。传到我这样的后进青年手里已经很晚了,我还没有资格往上面写字。陈俊社君跟我说,自己在看冯骥才的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,记录了很多人在“文革”中的经历。后来他似乎给我看了,当时彻底被震撼到了,感慨:“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!”从此,在我的世界里开了一扇天窗。
好玩的人
附中好玩的人太多了。比如每天开着电台广播大喊“同学们早饭一定要吃,要吃好,吃饱”的宿管老头。虽然我们也称他“老师”,毕竟没有那么尊敬,后来才知道,他竟然是复旦大学量子物理系毕业的,着实惊人。
记得有个同学说过:“高中物理没意思,很多都是错的。数学很重要,所以我现在在自学微积分。”老师竟然觉得高一高二随便他去就是了。这样的同学成绩固然不错,其实也不算最顶尖的。
还有一次一个很古板的英语老师说隔壁班一个女生,英语大概考了149分,自己也做不到,然后讲这个同学:“我上课她是不听的,但是遇到不知道的,马上就会记下来。”说得极其顺理成章,丝毫没觉得这个同学有什么“不敬”。
足球比赛是校园最大的盛会。有一天早上语文课我在睡觉,语文老师蛮喜欢我,就跑过来悄悄说:“你怎么在睡觉?”我说早上踢球累了。老师竟然先问:“赢了吗?”我说就是训练。老师说:“好吧,那上课还是不要睡觉了。”
高三还有一次好像是综合课,我又在睡觉。老师下来逐一发卷子,走到我这里,甚至没有打扰我,就把卷子约起来,放在了我的边上。
还有一次政治课,我桌上放了一本《长恨歌》,封面是王安忆的头像,貌似还挺美的。政治老师跑过来,帮我把王安忆放下去,然后说:“不要看美女了,还是听我讲吧。”